今天我们深入的聊聊一个与每位公司股东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裁判规则最好的配资官网,在新《公司法》实施以后(2023.12.29发布|202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你可能正愁着想把手中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外部投资者,却担心其他股东从中作梗;或者你作为公司老股东,怕有人“空降”进来,打乱公司原有的人合氛围。无论是哪种情况,新《公司法》都将彻底改变旧有的游戏规则,带来一场实务层面的“大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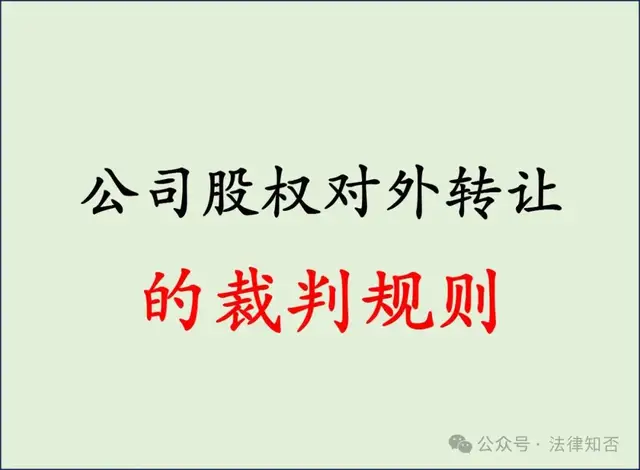
我们都知道,有限公司除了“资合性”(看重出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人合性”(看重股东间的信任和关系)。正因如此,过去对于股权对外转让,法律设置了重重关卡。但新法来临,这些关卡是拆了还是更高了?它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今天,我就为大家抽丝剥茧,逐一分析。
第一部分:旧规之困:股权转让的“卡脖子”时代
在2023年《公司法》修订前,我们主要依据的是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当时的股权对外转让,核心理念是“先同意(过半数股东同意),再通知购买(优先购买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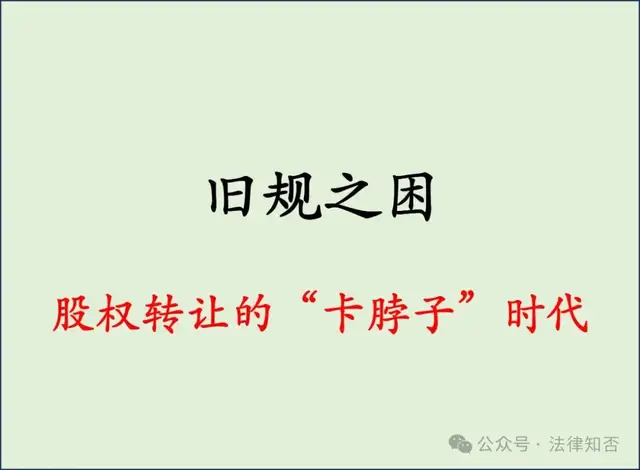
一、曾经的规则:先同意,再购买
▲2018年《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简单来说,就是:
1、想把股权卖给“外人”?先得兄弟们“点个头”!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其他股东同意你卖。30天内不吭声,就算同意了。
2、如果多数兄弟不同意?那他们就得自己掏钱买!不同意又不买,也算同意你卖。
3、同意卖了,但“外人”出的条件诱人?兄弟们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还进一步明确了这些程序和“同等条件”的判断标准(如数量、价格、支付方式、期限等)。
二、实务痛点:“既不买又不让卖”的困境
这种制度在实践中带来了不少麻烦,最让人头疼的是,当拟转让股东找到外部买家后,其他股东仅以“基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我们不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某个人(或某些人)”为由,却不明确表示购买,也拒绝提出合理条件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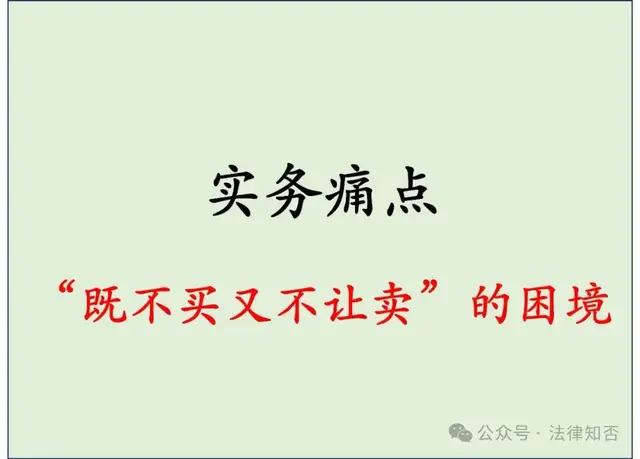
在2023年《公司法》修改前,法院对于这种“任性”拒绝往往陷入两难:既要保护股东的股权流转自由,又要尊重公司的人合性。最终,法院通常会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其他股东拒绝的理由是否“正当”。
案例分析:司法实践的无奈与判例指引
案例一:无理由拒绝,法院不予支持
在(2024)云01民终9219号《云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徐某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公司股东林某拟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徐某全。林某向其他股东发出通知后,对方明确表示“我不同意你转让给林银弟”,但却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购买。他们以一个与股权转让并无法律关联的“楚雄项目”问题,作为阻却转让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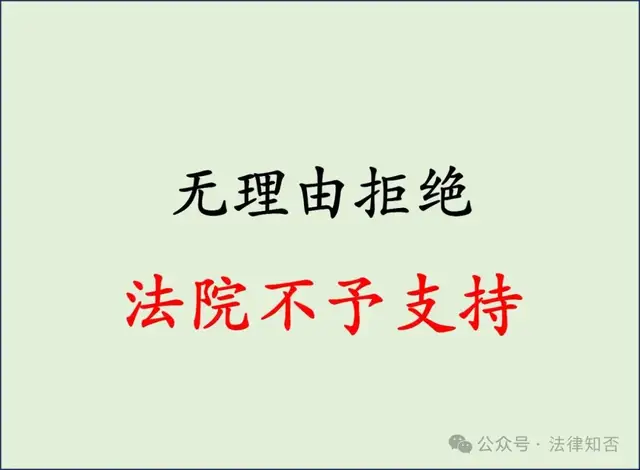
法院最终裁判:明确指出“转让股权与楚雄项目的解决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双方也未约定转让股权是以楚雄项目为前提,故叶某虎、李某枚并未在期限内购买股权,视为同意转让,不能以楚雄项目阻却林某转让股权。”
这个案例清晰地告诉我们,在旧法下,如果其他股东提出的异议与股权转让本身无关,且不履行购买义务,法院通常也会认定其放弃优先购买权,视为同意转让。
案例二:试图隐瞒或规避,结果适得其反
在(2024)苏03民终8305号《王某张某等股权转让纠纷》中,2014年王某(受让人)与张某(转让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又签订了一份《代持代购股权协议》,约定股权由张某代持,且“不得被外人所知”,意图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近十年后,张某试图履行通知义务时,其他股东才得知并主张优先购买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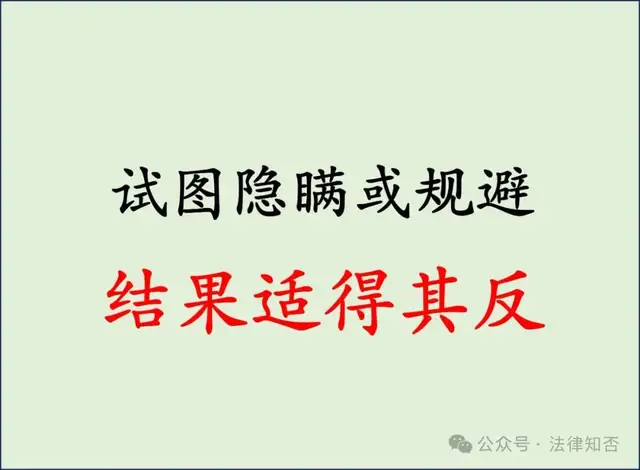
法院最终裁判:认定《个人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代持代购股权协议书》因其目的是向公司继续隐瞒股权转让事实,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目的不具有正当性,依法应认定无效。最终,由于其他股东行使了优先购买权,导致王某与张某的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被解除。
这个案例表明,旧法下试图通过隐瞒或“代持”等方式规避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往往会被法院认定其目的不具有正当性,相关规避行为无效,导致交易失败,甚至产生额外的纠纷。
第二部分:新规破局:2023年《公司法》的效率革命
2023年12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次修订,如同给股权对外转让这条路修了高速公路,大大提速,也更明确了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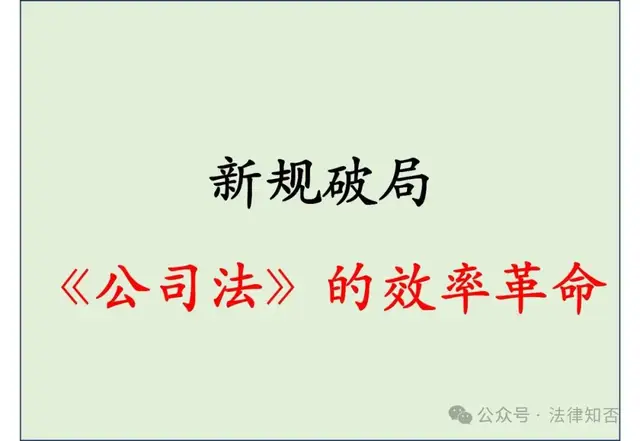
一、核心变化:从“同意权”到“优先购买权”的重心转移
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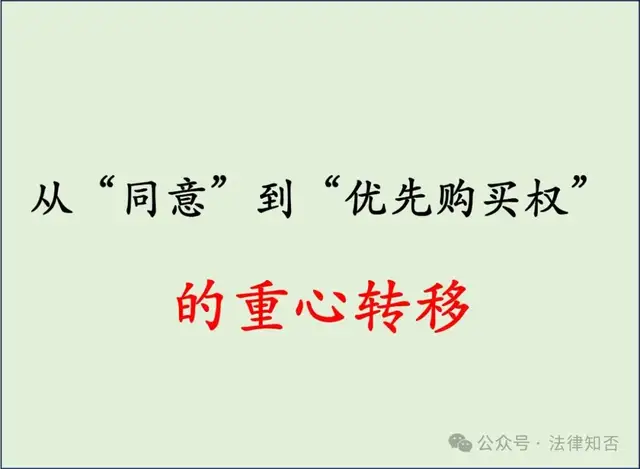
新旧法对比,最核心的变化是:
◆旧法:强调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在先。只有多数股东同意,或者虽然不同意但又放弃购买,才能对外转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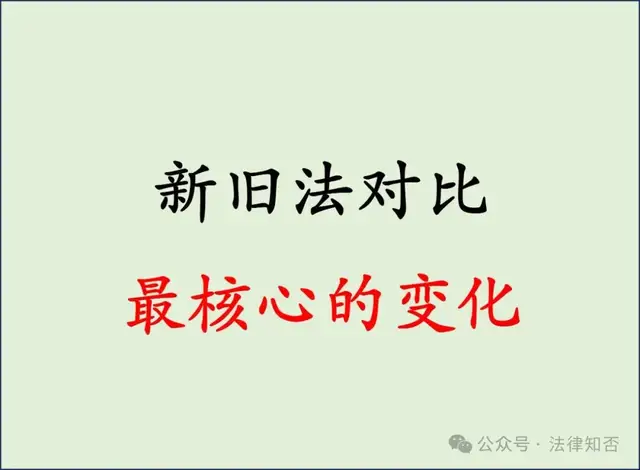
◆新法:彻底取消了“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一前置条件!拟转让股东只需要将股权转让的具体交易条件(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的权利重心直接转移到“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这意味着,你不用再担心其他股东以“人合性”为由,随便一句“不同意”就卡住你的股权转让了!
二、程序简化:30日内沉默即放弃,效率大幅提升
◆旧法:30日内不答复视为同意转让(针对“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则是在“同意转让”之后才能行使,整个流程耗时较长且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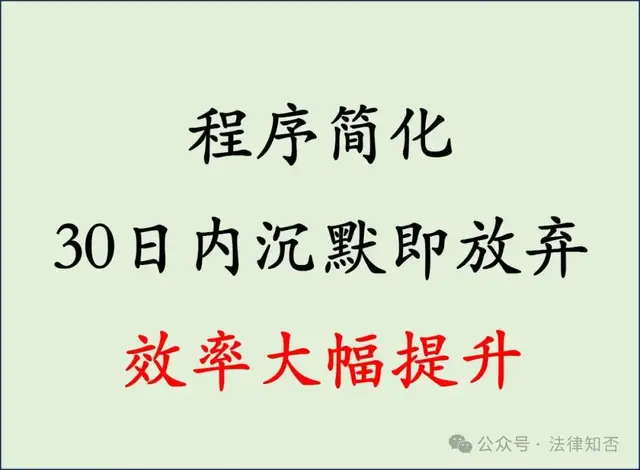
◆新法:明确规定,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这里的30天是针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且沉默即放弃。这极大地提高了股权转让的效率和确定性。
三、终结“任性”拒绝:无理阻碍不再有土壤
◆旧法下,正如前文所说,其他股东可以以“人合性”为由,不同意你将股权转让给某个人,即使他们不购买,也可能造成转让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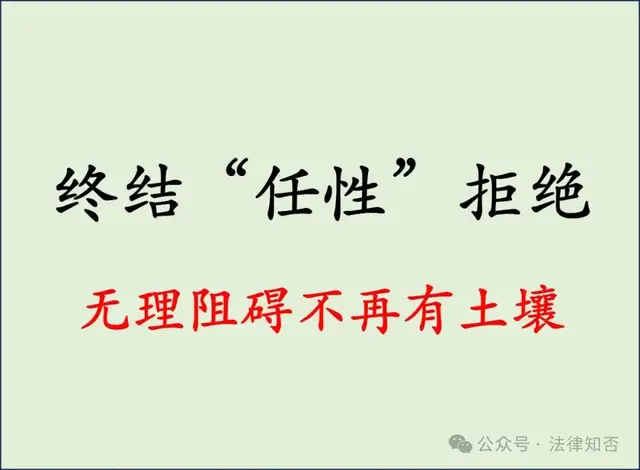
◆新法下,这种“既不买又不让卖”的任性行为,将彻底行不通了!因为新法不再要求其他股东“同意”转让,拟转让股东只需要履行“通知”义务,让其他股东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机会。只要拟转让股东找到了愿意以“同等条件”受让股权的外部方,且其他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那么拟转让股东就可以顺利完成对外转让。这意味着,股权对外转让的焦点,将从“你卖不卖给他”转变为“我买不买你的”。
第三部分:新规之下:司法实践的“变”与“不变”
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的修改,无疑将对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一、不变的原则:章程优先与“同等条件”的考量
1、“同等条件”的判断依然重要。尽管新法没有直接提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但其关于“同等条件”的考量因素(数量、价格、支付方式、期限等)仍然是法院在判断优先购买权是否被侵犯时的重要依据。拟转让股东在通知其他股东时,仍需详细列明这些条件,以确保其通知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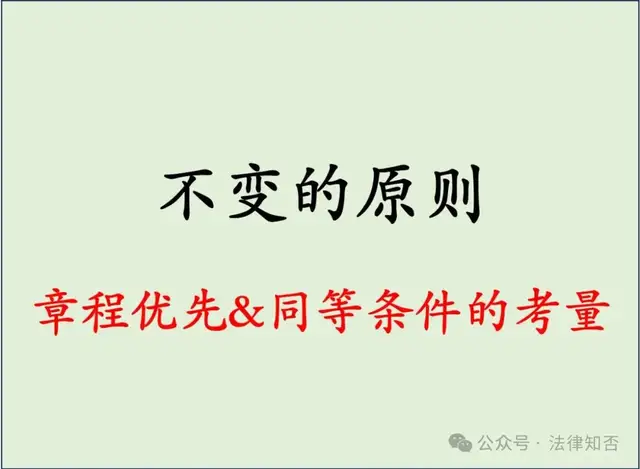
2、公司章程的优先性。新《公司法》第八十四条同样保留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原则。这意味着,公司章程仍然是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小宪法”。如果章程中有更严格或更灵活的规定(例如,规定了更长的答复期限、更严格的通知方式,或者更具体地界定了“同等条件”),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仍会尊重章程的约定。
二、变化的审判:聚焦通知与权利行使
法院在审理股权对外转让纠纷时,将不再纠缠于“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这个环节,而是直接聚焦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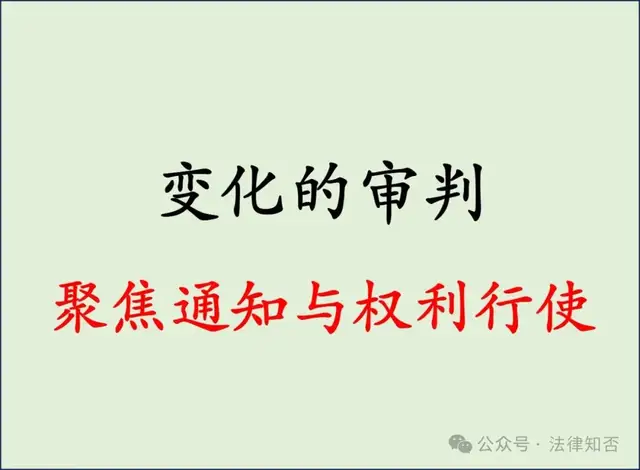
拟转让股东是否履行了书面通知义务,通知内容是否包含了股权转让的具体交易条件(数量、价格、支付方式、期限)?
其他股东是否在接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明确行使了优先购买权,并表示愿意在“同等条件”下购买?
如果存在两个以上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是否按照章程、协商或出资比例确定了购买比例?
案例分析:新法实施后的裁判新风向
案例三:通知时间晚于签订合同,但优先购买权未受损,法院支持转让
在(2025)黔05民终7876号《李某荣与许某纳雍县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纠纷》中,李某(转让人)与许某(受让人)于2022年11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李某于2023年6月23日才通过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其他股东其拟对外转让股权。虽然通知时间晚于合同签订,但其他股东并未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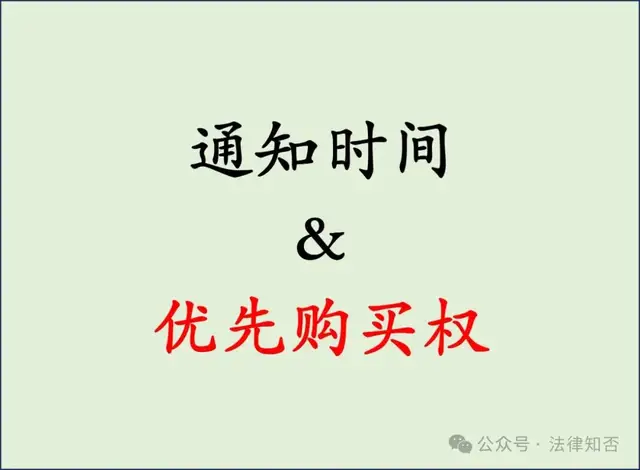
法院最终裁判:认定一审法院关于李某未履行通知义务的认定不当。法院明确指出,李某转让股权并未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并无优先购买的意愿,故李某可以要求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这个案例表明,在新法(及其适用规则)下,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可以先于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只要后续通知程序履行到位且其他股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交易即可有效进行,且法院会支持变更登记。这大大简化了交易程序,提升了效率。
案例四:隐名股东转让股权,通知时滞,只要权利保障仍有效
在(2025)川3401民初4453号《李某龚某合同纠纷》中,李某作为某公司的隐名股东,在2022年10月1日与龚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直至2024年9月27日,才由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李某转让股权给龚某,并放弃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以李某不具备股东资格且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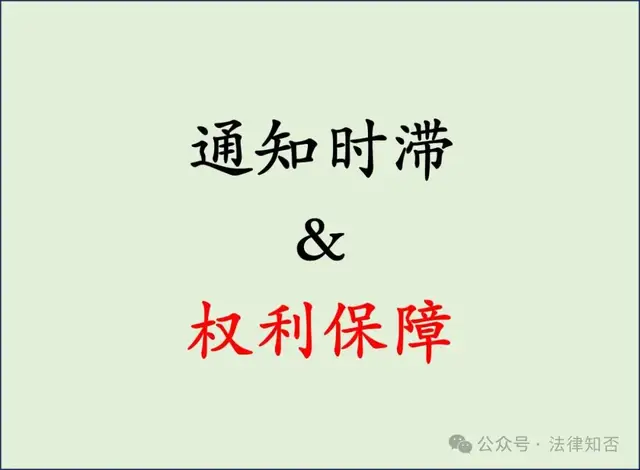
法院最终裁判: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判决。虽然李某未直接提交其与龚某签订协议时已取得登记股东同意的证据,但《公司法》并未禁止隐名股东转让股权。法院认为,即使李某在签订协议时未取得登记股东的同意,协议也只是“成立但未生效”,而非“无效”。只要登记股东明确表示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协议就能够生效。因本案中后续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故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龚某要求退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例进一步强化了新法下“通知义务”的中心地位。它表明,即便存在隐名股东、通知存在时滞,只要最终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未被实际侵害,且他们放弃了该权利,股权转让合同仍然可以被认定有效。法院的审查重心放在了实质权利的保障,而非严格的形式合规性。
案例五:股权转让后公司拒绝变更登记,不能直接解除合同,受让人可另案诉讼公司
在(2025)豫13民终1300号《南阳某有限公司刁某保股权转让纠纷》中,刁某某(转让人)与某甲公司(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某甲公司已支付大部分转让款并实际使用了一条生产线。但股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原因是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某不同意。某甲公司因此诉请解除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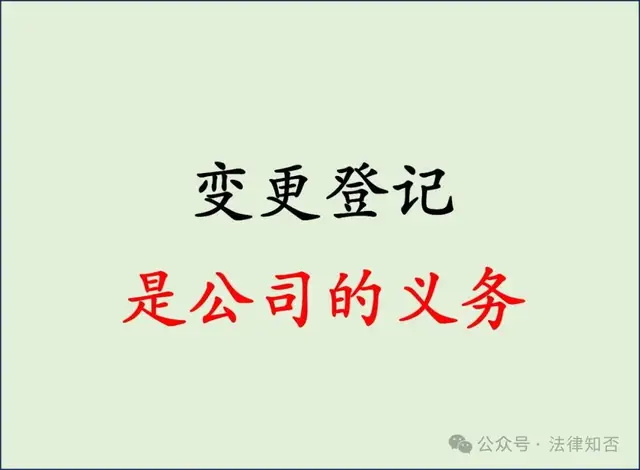
法院最终裁判:驳回了某甲公司的解除协议诉请。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股权未能变更登记的原因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同意,而非刁某某原因。法院明确指出,某甲公司可以请求公司协助变更登记,若公司拒绝,可以另行提起诉讼。
这个案例进一步说明,新法下股权转让的重心在于保障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合同效力。只要优先购买权问题得到解决,公司应配合办理登记。公司不配合,受让人可以起诉公司要求办理,而不能轻易解除与转让方的合同。
这些案例,虽然事实行为发生在2024年7月1日新法实施之前,但在裁判时间上已进入新法实施阶段,其裁判思路和规则明显吸收了新法理念,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司法实践的方向。
结语:明晰权利边界,把握未来机遇
新《公司法》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改革,体现了立法者在“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它更侧重于保障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股权的流转效率,同时通过强化优先购买权来维护现有股东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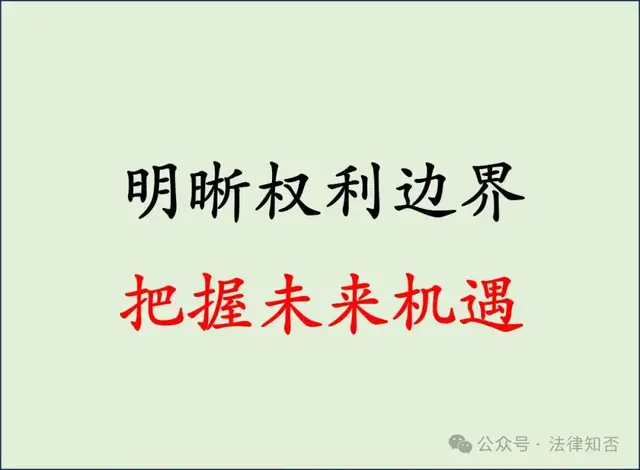
●对于拟转让股权的股东:您的权利更大了,但通知义务也更具体、更严格了。详细、及时地披露交易条件,是确保您顺利转让的关键。即使在签订合同后才通知,只要能确保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未受损,交易仍可有效推进。
●对于其他股东:您的责任更大了,如果想保住“圈子”或者扩大持股比例,就必须在收到通知后,迅速评估并果断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机会稍纵即逝。被动等待或含糊其辞,将不再有“卡脖子”的功效。
●对于公司章程的制定者:章程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您可以通过章程对股权转让(包括优先购买权行使细节、期限等)进行更个性化、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约定,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为公司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新法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股权转让的最新规则,务必、务必、务必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保障您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更多细节】请参阅原文最好的配资官网
睿迎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